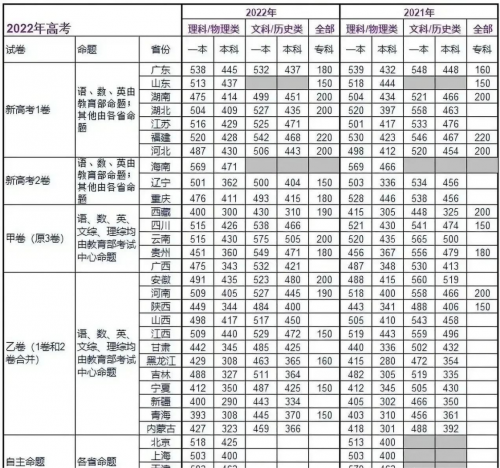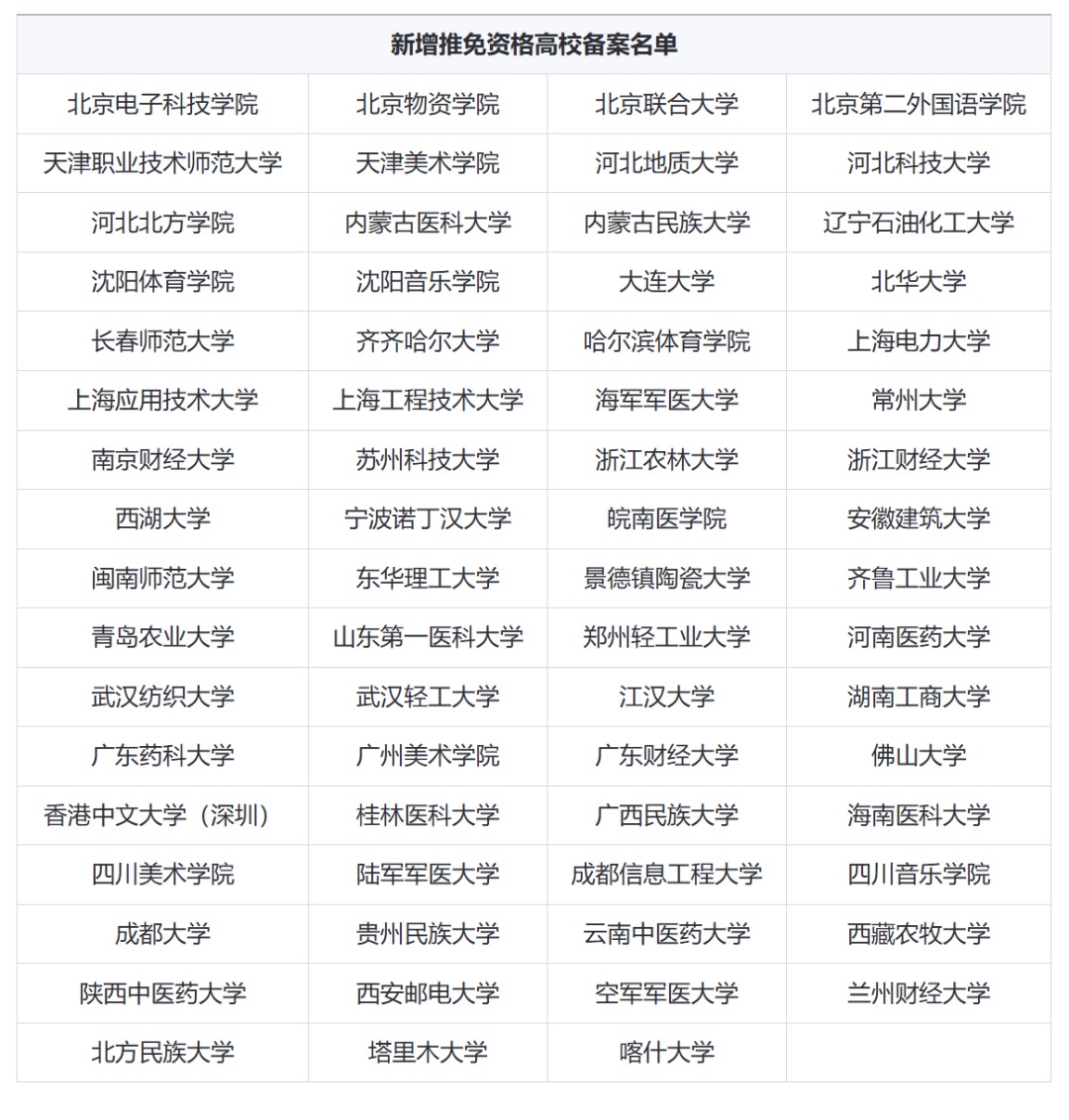北京的晨光刚漫过小区的树梢,一场期待已久的从北方到西南的自驾旅程,就随着发动机的轻响启程了。

车窗外的风景渐渐变换,从北京的高楼换成华北平原的麦田,再到河南许昌的胖东来广场时,天色已暗。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了家民宿,打开窗户,让夏夜的风带着远处小吃摊的香气飘进来。弟弟和表弟躺在床上,对着地图上蜿蜒的路线争论明天的美好旅行。聊着聊着就进入了梦乡。
第二日清晨继续南下,高速路边的山越来越青,空气里的湿润感也越来越浓。刚驶进湖北宜昌城区,打开车窗一股燥热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们导航到姑父早已定好的酒店,等推开酒店江景房的门,我们都忍不住惊呼:长江像一条碧绿的绸带铺在眼前,远处的三峡大坝在薄雾中露出轮廓,江面上的货轮缓缓驶过,留下长长的水痕。

歇了半个钟头,我们便去了大坝上游的木鱼岛公园。这小岛像块绿宝石嵌在江里,道路沿着江岸蜿蜒,踩上去咯吱作响。爷爷牵着奶奶的手走在前面,指着江水念叨:“这水可真壮观啊。”我和爸爸站在岛尖,看江水裹挟着浪花向东奔涌,弟弟和表弟则趴在草地上,对着江里游泳的人喊加油——那些游泳爱好者在江水中舒展四肢,像一群自在的鱼,引得表弟也吵着说要学游泳。
宜昌的长江,是刚柔相济的画卷。上游来的江水还带着三峡的奔涌,到了这里便放缓脚步,江面豁然开阔,像一匹被摊开的碧绸,映着两岸的山林与沿江而建的城市。

江风裹着水汽掠过,岸边的芦苇荡翻起白浪,空气也似乎不那么燥热了,远处的西陵长江大桥如长虹卧波,钢索在蓝天下拉出优美的弧线,桥上车流如织,与江面上缓缓航行的货轮,构成了动与静的和谐对话。
夕阳西下,江面便染成琥珀色,江堤上的人渐渐多了,有散步的老人,又有奔跑的小孩,既有大江奔涌的底色,又藏着人间烟火的温柔。
观赏完大江的景色,姑姑带我们去了江边的一家餐馆。热锅端上来时还滋滋作响,鲜美的鱼肉浸在乳白的汤汁里,撒上翠绿的葱花,香气瞬间钻满鼻腔。弟弟和表弟顾不上烫,夹起一块就往嘴里送,烫得直吸气却又停不下筷子。每个人的嘴角都沾着笑意。回到酒店,打开窗子吹着风。江面上的灯光次第亮起,倒映在水里像一串流动的星子。我忽然觉得,这场旅程最动人的不是风景,而是身边这些人的陪伴——是爸爸开车时专注的侧脸,是爷爷奶奶相握的手,还有弟弟表弟清脆的笑声。这些细碎的温暖,都藏在宜昌的江风里,成了云贵川之旅最难忘的开篇。

云贵之旅第二天:长江三峡大坝
云贵之旅的第二天,晨光刚漫过酒店窗户,我早已按捺不住对三峡大坝的向往。我们匆匆扒完早餐,脚步追着心,直奔那处藏在群山与大江间的奇迹。
摆渡车在阳光里穿行,爷爷望着远处隐约的大坝轻声说:“当年修大坝时,多少人从五湖四海赶来。”不一会车已停在售票处前。跟着参观的人流办完手续,换乘的观光车沿着盘山公路向上,窗外的长江渐渐从一条银带,铺成了眼前浩浩荡荡的碧波。

最终停在船闸与大坝之间的山巅时,我扶着观景台的栏杆望去,三峡大坝像一条钢铁巨龙横卧江面,坝体上“三峡大坝”四个红色大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诗句中“衔远山,吞长江,浩浩汤汤,横无际涯”此刻得到了具象化。无数巨轮穿过坝体,轰鸣声隔着几百米仍震得人胸口发颤。爸爸指着下方错落的闸门,给我们讲五级船闸的原理:“船要过坝,得像走楼梯一样,一级级升上去,再一级级降下来,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闸呐。”
表弟和弟弟踮着脚数闸门的层数,爸爸则举着相机,想把大坝、江水与远处的青山都框进镜头里。是啊,眼前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长江,曾载着商船与渔舟,也曾在汛期里咆哮着威胁两岸;而如今,这座大坝让江水驯服,让电能跨越千山万水,让航船平稳地穿梭于长江上下游。这哪里是一座水利工程和雄伟建筑,分明是一代代人用智慧与汗水,给祖国的山河写下的壮丽诗篇。

风继续吹着,江声浩荡。我望着脚下奔涌的长江,望着远处巍峨的大坝,忽然懂得了“国之重器”这四个字的分量。它不是书本上冰冷的词语,是此刻震耳的巨响。这趟云贵川之旅的第二天,三峡大坝与长江,给了我最生动的一课——关于祖国的辽阔与强大,关于每一寸山河里,都藏着的中国人的坚韧与智慧。
云贵之旅第三天 织金洞
云贵之旅的第三天,我们终于踏上了贵州的土地。早餐后,我们一同向着织金洞出发,车窗外的山景逐渐从清秀转向奇崛,心里的期待也跟着一点点升温。

抵达景区时,山间的风还带着晨雾的微凉。沿着石阶往山腰走,远远便望见那处被群山环抱的洞口——不是想象中的小巧模样,而是像山被生生劈开一道巨口,黑黢黢的洞口吞纳着天光,站在入口处往下望,只能看见层层叠叠的石阶蜿蜒伸入黑暗,耳边满是其他游客的惊叹与脚步声。
跟着人流往下走,越往深处,空气越凉得刺骨。下到洞底时,脚边忽然泛起一片暗沉的光,低头才发现是一滩河水,水面像蒙了层墨,映着洞顶垂下的石笋,竟透出几分诡异的静。可这静很快就被前方的景象冲散了——转过一道石墙,眼前骤然亮了起来。
五彩的灯光从不同角度打在钟乳石上,像是给冰冷的岩石注入了生命。最显眼的是那根“擎天柱”,从洞底直直向上,顶端与洞顶相连,表面的纹路像流水凝固的痕迹,乳白与浅黄交织,灯光下泛着细腻的光泽,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淌下蜜来。旁边的“灵芝仙草”更妙,一片片石瓣向外舒展,边缘泛着淡淡的紫色,根部却嵌在深褐的岩石里,像是从千年的时光里刚冒出来的灵气。

我们沿着步道慢慢走,目光根本挪不开。有的钟乳石像仙女的裙摆,层层叠叠垂落,;有的则像猛兽的利爪,尖锐的石尖朝着地面,还有那片“石帘洞”,无数细长的石条从洞顶垂下,密得像帘子,灯光穿过石条的缝隙,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,
弟弟忽然指着一处小声喊我们,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,只见两尊钟乳石隔岸相对,一尊细长如笔,一尊宽扁如纸,灯光下,“笔”的顶端泛着金色,“纸”的表面则是均匀的乳白,像是谁把“妙笔生花”四个字刻进了这山洞里面的。我伸手碰了碰身边的一块钟乳石,指尖传来冰凉的硬,可看着它晶莹剔透的模样,又觉得它是软的、活的。
走出织金洞时,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。有一种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感觉。回头望那黑漆漆的洞口,忽然觉得刚才在洞里的所见像一场梦——那些流光溢彩的钟乳石,那些藏在岩石里的时光,都静静躺在贵州的山腹里,等待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们,去读它千百万年的故事。

多彩贵州第二天 百里画廊
织金洞的钟乳奇观还在脑海中流转,我们便已踏上了前往百里画廊的旅程。车在山间盘旋片刻,一汪碧绿的江水突然撞入眼帘,码头边的石阶被江风浸得微凉,我们便攥着温热的船票在岸边等候。
踏上游船的瞬间,江风便裹着水汽扑来。船身破开镜面般的江水,留下两道细碎的波纹,两岸的青山立刻成了移动的画框。山是像是被墨汁浸润后又轻轻晕开,山壁上裸露的岩层却呈着浅灰和褐色,像是大自然用刻刀随意勾勒的线条。有的山体直插江面,岩石狰狞如兽;有的则缓坡而下,覆盖着青绿的草木,连风掠过都带着草木的清香。

行至半途,船头突然传来惊呼——前方山体竟被生生凿开一个巨洞,洞口高阔得能容下整艘游船。再看右侧江岸,两座山峰并肩而立,峰顶圆润隆起,竟像极了骆驼背上的双峰,连线条的弧度都那般逼真,仿佛下一秒便会迈开蹄子踏江而去。
继续向前,岸边的景致更添生机。青灰色的田埂间,农人弯腰种作,不远处的草地上,几头黄牛甩着尾巴啃草。江水倒映着青山、田梗与牛群,一片和谐美丽。
下船时,我的脚步仍有些轻盈,仿佛还在江面上轻轻摇晃。回望那片山水,青山仿佛真的成了五彩斑斓的画廊,农人的身影与牛群都成了画中的点缀。那一刻,唯有心中翻涌的震撼久久不散——原来祖国的山河,竟能美到让人心尖发颤,让每一次呼吸都成了对美好世界的致敬。

七彩云南第一天 茶马古道小院
车轮越过黔滇边界的界碑时,风里的气息悄然变换——贵州山间的湿润雾气淡了,取而代之的是云南阳光晒过的干爽,姑父驾车在大理剑川盘山路上蜿蜒,直到暮色,一座藏在茶马古道林间的农家小院才映入眼帘。茶马古道马锅头叔叔的院子小而精,有着小小的池塘、小小的石桥,栅栏上爬着细碎的蓝花,楼梯转角摆着几盆兰草,茶马古道收藏室里的老物件在灯下静默,向我们述说着古道岁月的沧桑、不平凡和繁华过后的宁静与安然。我们卸下旅途一天的疲惫,在这茶马古道山中小院的静谧里歇了一夜。
七彩云南第二天 和家恩道庄园
次日上午,我们来到了和叔叔、和爷爷的“和家恩道”苹果庄园,中午时分,和家爷爷奶奶做了很多白族家乡美食,席间还听到原生态的山歌“五朵金花”和白家祝酒歌,真是悦耳动听,情真意切,浓浓的民族风情。
午餐后,我们一大群人笑着拎起竹篮:往山谷里走,一条小溪顺着田埂流淌。果林就藏在山谷间,苹果树不高,枝头挂满了果子,因为刚下过雨的缘故,滴滴水珠还在果皮上流淌,看着更加诱人了,采上一个,咬一口,汁水充斥着口腔,沁人心脾。采够了果子,我和表弟干脆躺在溪边的草地上,草叶蹭着脸颊,风里满是果香与泥土的气息,大家一脸满足,笑声歌声在山谷里轻轻回荡。

采完了苹果,我们临时起意去采蘑菇。松针铺成的“地毯”软乎乎的,拨开层层针叶,便能看见顶着白伞盖的小蘑菇——有的菌柄泛着淡粉,有的伞沿镶着褐色边,像撒在林间的彩色纽扣。我们互相攀比,不多时竹筐就装得半满。
傍晚赶到沙溪古镇,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,茶马古道的马蹄印似还嵌在缝里。我们来到了老戏台的飞檐挑着暮色,檐角铜铃被风一吹,戏台旁站着一个人,他是沙溪卓别林,他是一个坚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行走在人间的艺术家。他一次次做出搞怪的动作,逗的我们和来往的行人哈哈直笑,仿佛真的卓别林,有他在,沙溪古镇更增添了一分欢乐,他爱这片土地,更用爱感染着来到这里的人。玉津桥横跨在江水上,桥身的青苔浸着江水的凉,远处青山如黛,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声漫过石桥,连时光都在这古镇的光影里慢了下来。
夜色渐深,我们住进了沙溪卓别林的彝族山庄。身着特色服饰的彝族人民手拉手,肩搭肩欢快的舞蹈着,欢乐的氛围弥漫着,每个人脸上都已洋溢着笑容,此刻我们好像就是一家人一样。的歌声清亮动人,一天的劳累似乎都消失了。不久饭菜就做好了,圆桌上摆满了腊肉、山鸡和荞面粑粑。吃完农家乐后,大家便拉起手,围成一个大圆圈,跳起彝族篝火舞。灯光映着彝族同胞淳朴的笑脸,我的手被他们紧紧握着,温暖从指尖传到心底。那一刻忽然明白,所谓民族团结,从不是遥远的话语,而是此刻相拥的双手、贴心的温暖和感动,是从千里之外,南来北往不同民族、不同肤色的人,因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而命运相连的真诚。
这一路走来,往返行程6800余公里,多彩贵州和七彩云南的美刻在茶马古道的石板路上,刻在老君山山谷的果林里,藏在沙溪古镇的飞檐间,更融在多民族同胞传递来的温暖里。大好河山滋养了祖国西南这片神奇的土地,她美丽、富饶、灵秀、活力、和美,而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多民族同心的温暖,让这份研学旅行的美好有了更动人的旋律和份量。